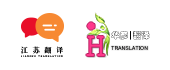究其原因,读英文的直接作用,看翻译的间接默化,都有影响。所谓翻译,并不限于译书与译文,凡举报纸、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介惯用的译文体,也不无污染之嫌。有时候,文言也可以西化的。例如“肯尼迪总统曾就此一举世瞩目之重大问题,与其白宫幕僚作深夜之紧急商讨”一句,便是半吊子文言纳入西文句法后的产品。
中文通达的人面对无所不在的译文体,最多感到眼界不清、耳根不静,颇为恼人。中文根底原就薄弱的人,难逃这类译文体的天罗地网,耳儒目染,久而习于其病,才真是无可救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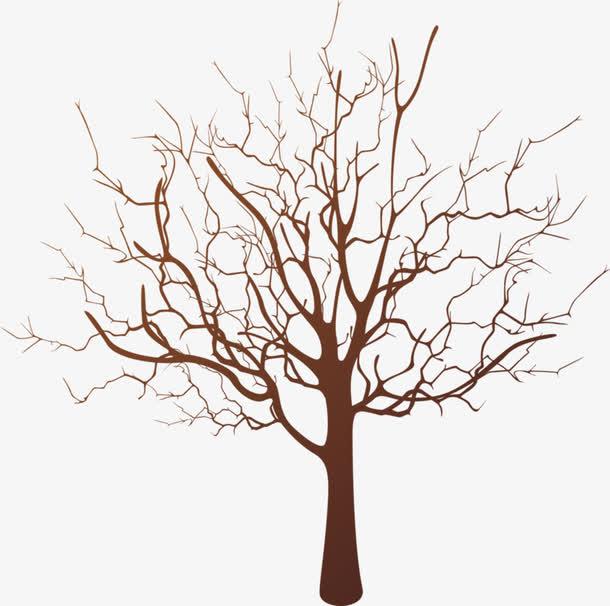
我曾另有文章抽样评析成名作家笔下西化的现象,下文我要从目前流行的西化用语和句法之中,举出一些典型的例子来,不但揭其病状,还要约略探其病根。我只能说“约略”,因为目前恶性西化的现象,交茎牵藤,错节盘根,早已纠成了一团,而溯其来源,或为外文,或为劣译,或为译文体的中文,或则三者结为一体,混沌而难分了。
(一)那张唱片买了没有?
买了(它了)。
(它)好不好听?
(它)不太好听。
(二)你这件新衣真漂亮,我真喜欢(它)。
(三)他这三项建议很有道理,我们不妨考虑(它们)。
(四)花莲是台湾东部的小城,(它)以海景壮美闻名。
(五)舅舅的双手已经丧失了(它们的)一部分的灵活性了。
西化病状很多,滥用代名词是一种。前面五句括弧里的代名词或其所有格,都是多余的,代名词做受词时更常省去。文言里的“之”却是例外:李白诗句“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正是如此。第五句整句西而不化,问题还不止于滥用代名词所有格。其实“还原”为自然的中文,无非是“舅舅的双手已经有点不灵了”。
(六)一年有春、夏、秋和冬四季。
(七)李太大的父亲年老和常生病。
(八)我受了他的气,如何能忍受和不追究?
(九)同事们都认为他的设计昂贵和不切实际。
目前的中文里,并列、对立的关系,渐有给“和”字去包办的危机,而表示更婉转更曲折的连接词如“而”、“又”、“且”等,反有良币见逐之虞。这当然是英文的and在作怪。在英文里,名词与名词、形容词与形容词,副词与副词,甚至介系词与介系词,一句话,词性相同的字眼之间,大半可用and来连接,但在中文里,“和”、“及”、“与”等却不可如此揽权。中文说“笑而不答”,“顾而乐之”,“顾左右而言他”,何等顺畅;一旦西化到说成“笑但不答”,“顾与乐之”,“顾左右以及言他”,中文就真完了。
此外,中文并列事物,往往无须连接词,例如“生老病死”、“金木水火土”等,都不应动员什么连接词。句六当然应删去“和”字。句七可作“年老而多病”或“年老多病”。句八可以“而”代“和”,句九亦然。
(十)(关于)王教授的为人,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十一)你有(关于)老吴的消息吗?
(十二)(关于)这个人究竟有没有罪(的问题),谁也不敢判断。
介系词用得太多,文句的关节就不灵活。“关于”、“有关”之类的介系词在中文里越来越活跃,都是about、concerning、with regard to等的阴影在搞鬼。前面这三句里,删去括弧内的字眼,句法一定干净得多。有人曾经跟我抬杠,说“关于老吴的消息”是听别人说的,而「老吴的消息」是直接得自老吴的,怎可不加区别?英文里hear from和hear of确是判然有别,但在中文里,加不加“关于”是否可资区别,却不一定。加上“关于”,是否就成间接听来,不加“关于”,是否就来自老吴自己,在中文里还作不得准。所以这一点“精密”还只是幻觉。
(十三)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怎能不爱中国?
(十四)作为一个丈夫的他是失败的,但是作为一个市长的他却很成功。
(十五)缇萦已经尽了一个作为女儿的责任了。
表示身份的介系词早已渗透到中文里来了。其实在中文里,本来只用一个“做”字。句十四大可简化成:“他做丈夫虽然失败,做市长却很成功。”句十五也可改为:“缇萦已经尽了做女儿的责任了。”句十三的毛病,除了“作为”之外,还有单复数不相符合,最自然的说法该是:“身为中国人,怎能不爱中国?”
(十六)(对于)这件事,你们还没有(作出)决定吗?
(十七)敌方对我们的建议尚未作出任何的反应。
(十八)对法西斯的暴政他(作出)强烈抗议。
(十九)报界对这位无名英雄一致作出哀痛与惋惜。
(二十)兄弟两人争论一夜,最后还是哥哥(作出)让步。
在英文里,许多东西都可以“作出”来的:赚钱叫“做钱”,求欢叫“做爱”,眉目传情叫“做眼色”,赶路叫“做时间”,生火叫“做火”,生事叫“做麻烦”,设计叫“做计划”,决策叫“做政策”。在中文里,却不是这种做法。近年来,“作出”一语日渐猖獗,已经篡夺了许多动词的正位。
这现象目前在祖国大陆上最为严重,香港也颇受波及。结果是把许多现成而灵活的动词,贬成了抽象名词,再把这万事通的“作出”放在前面,凑成了一个刻板无趣苍白无力的“综合动词”。以前“建议”原是自给自足独来独往的动词——例如“他建议大家不妨和解”——现在却变成了“作出建议”综合动词里的受词。
其实“建议”之为动词,本来就已是一个动词(建)加名词(议)的综合体,现在无端又在前面加上一个极其空泛的动词(作出),不但重复,而且夺去了原来动词的生命,这真是中文的堕落。近年来这类综合动词出现在报刊和学生习作之中,不一而足:硬牵到“作出”后面来充受词的字眼,至少包括“主动”、“贡献”、“赞叹”、“请求”、“牺牲”、“轻视”、“讨论”、“措施”等等,实在可怕!其实这些字眼的前面,或应删去这万恶的“作出”,或应代以他词。例如“采取主动”,“加以讨论”,“极表轻视”,就比漫不经心地代入公式来得自然而道地。
在现代英文里,尤其是大言夸夸的官样文章,也颇多这种病状:《一九八四》的作者奥威尔在《政治与英文》(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George Orwell)里早已慨乎言之。例如原来可用单纯明确的动词之处,现在大半代以冗长杂凑的片语,原来可说cause,现却说give rise to;同样地,show,lead,serve to,tend to等也扩充门面,变成了make itself felt,play a leading role in,serve the purpose of,exhibit a tendency to,奥威尔把prove,serve,form,play,render等一拍即合的万能动词叫“文字的义肢”(verbal false limb)。“作出”正是中文里的义肢,装在原是健全却遭摧残的动词之上。
(二十一)杜甫的诗中存在着浓厚的人民性。
(二十二)台北市的交通有不少问题(存在)。
(二十三)中西文化的矛盾形成了代沟(的存在)。
(二十四)旅伴之间总难免会有磨擦(的发生)。
(二十五)我实在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香港(的原因)。
“有”在中文里原是自给自足的大好动词,但早期的新文学里偏要添上蛇足,成为“有着”,甚至“具有着”,已是自找麻烦。西化之后,又有两个现象:一是把它放逐,代以貌若高雅的“存在”;一是仍予保留,但觉其不堪重任,而在句末用隆重的“存在”来镇压。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存在主义”吧。句二十一中“存在着”三字,本来用一个“有”字已足。不然,也可用“富于”来代替“存在着浓厚的”。至于句二十四末之“发生”及句二十五末之“原因”,也都是西化的蛇足,宜斩之。
(二十六)截至目前为止,劫机者仍未有明确的表示。
(二十七)《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名剧(之一)。
(二十八)李白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二十九)在一定的程度上,我愿意支持你的流行歌曲净化运动。
(三十)陈先生在针灸的医术上有一定的贡献。

英文文法有些地方确比中文精密,但绝非处处如此。有时候,这种精密只是幻觉,因为“精密”的隔壁就住着“繁琐”。中文说“他比班上的同学都强”,英文却要说“他比班上的任何其他同学都强”。加上“任何其他”,并不更精密多少,就算精密一点,恐怕也被繁琐抵消了吧。英文的说法,如果细加分析,当会发现“任何”的意思已经包含在“都”里;至于“其他”二字,在表面上的逻辑上似乎是精密些,但是凭常识也知道;一个学生不会比自己强的。
同样,英文说“汉城气候比台北的(气候)热”,也不见得就比中文的“汉城的气候比台北热”精密多少。句二十六之首六字如改为“迄今”,意义是一样的。句二十七删去“之一”,毫无损失,因为只要知道莎士比亚是谁,就不会误会他只有一部名剧。句二十八如写成“李白是中国的大诗人”或者“李白是中国极伟大的诗人”,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英文“最高级形容词+名词+之一”的公式,其客观性与精密性实在是有限的:除非你先声明中国最伟大的人在你心目中是三位还是七位,否则李白这“之一”的地位仍是颇有弹性的,因为其他的“之一”究竟有多少,是个未知数。所以“最伟大的某某之一”这公式,分析到底,恐怕反而有点朦胧。
至于“之一”之为用,也常无必然。例如“这是他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就等于“这是他所以失败的一个原因”,因为“一个原因”并不排除其他原因。如果说“这是他所以失败的原因”,里面这“原因”就是唯一无二的了。同样,“这是他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可说成“这是他所以失败的一大原因”。
至于句二十九,有了句首这七字,反而令人有点茫然,觉得不很“一定”。这七字诀的来源,当是to a certain degree,其实也是不精密的。如果说成“我愿意酌量(或者:有限度地)支持你的……运动”,就好懂些了。句三十里的“一定”,也是不很一定的。
中文原有“略有贡献”、“颇有贡献”、“甚有贡献”、“极有贡献”、“最有贡献”之分;到了“一定的贡献”里,反而分不清了。更怪的用法是“他对中国现代化的途径有一定的看法”。附带可以一提,“肯定”原是动词,现在已兼营副词了。我真见人这么写过:“你作出的建设,肯定会被小组所否定。”前述“一定”和“肯定”的变质,在祖国大陆上也已行之有年,实在令人忧虑。
(三十一)本市的医师(们)一致拒绝试用这新药。
(三十二)所有的伞兵(们)都已安全着陆。
(三十三)全厂的工人(们)没有一个不深深感动。
中文西化以前,早已用“们”来表示复数:《红楼梦》里就说过“爷们”、“丫头们”、“娼妇们”、“姑娘们”、“老先生们”,但多半是在对话里,而在叙述部分,仍多用“众人”、“众丫鬟”、“诸姐妹”等。现在流行的“人们”却是西化的,林语堂就说他一辈子不用“人们”。其实我们有的是“大家”、“众人”、“世人”、“人人”、“人群”,不必用这舶来的“人们”。“人人都讨厌他”岂不比“人们都讨厌他”更加自然?句三十一至三十三里的“们”都不必要,因为“一致”、“所有”、“都”、“全厂”、“没有一个不”等语已经表示复数了。
(三十四)这本小说的可读性颇高。
(三十五)这家伙说话太带侮辱性了。
(三十六)他的知名度甚至于超过了他的父亲的知名度,虽然他本质上仍是一个属于内向型的人。
(三十七)王维的作品十分中国化。
中文在字形上不易区别抽象名词与其他词性,所以a thing of Beauty和a beautiful thing之间的差异,中文难以翻译。中文西化之后,抽象名词大量渗入,却苦于难加标识,俾与形容词、动词等分家自立。英文只要在字尾略加变化,就可以造成抽象名词,甚至可以造出withness之类的字。
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术语传入中国或由日本转来之后,抽象名词的中译最令学者头痛。久而久之,“安全感”、“或然率”、“百分比”、“机动性”、“能见度”等词也已广被接受了。
我认为这类抽象名词的“汉化”应有几个条件:一是好懂,二是简洁,三是必须。如果中文有现成说法,就不必弄得那么“学术化”,因为不少字眼的“学术性”只是幻觉。句三十四其实就是“这本小说好看”。句三十五原意是“这家伙说话太无礼”或“这家伙说话太侮辱人了”。跟人吵架,文绉绉还说什么“侮辱性”,实在可笑。句三十六用了不少伪术语,故充高级,反而啰嗦难明。究其实,不过是说:“他虽然生性内向,却比他父亲还更有名。”16个字就可说清的意思,何苦扭捏作态,拉长到36个字呢?句三十七更有语病,因为王维又不是外国人,怎么能中国化?发此妄言的人,意思无非是“王维的作品最具中国韵味”罢了。
(三十八)这一项提案已经被执行委员会多次地讨论,而且被通过了。
(三十九)那名间谍被指示在火车站的月台上等候他。
(四十)这本新书正被千千万万的读者所抢购着。
(四十一)基辛格将主要地被记忆为一位翻云覆雨的政客。
(四十二)他的低下的出身一直被保密着,不告诉他所有的下属。
英语多被动语气,最难化入中文。中文西化,最触目最刺耳的现象,就是这被动语气。无论在文言或白话里,中文当然早已有了被动句式,但是很少使用,而且句子必短。例如“为世所笑”、“但为后世嗤”、“被人说得心动”、“曾经名师指点”等,都简短而自然,绝少逆拖倒曳、喧宾夺主之病。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除了“被”、“经”、“为”之外,尚有“受”、“遭”、“挨”、“给”、“教”、“让”、“任”等字可以表示被动,不必处处用“被”。
其二是中文有不少句子是以(英文观念的)受词为主词:例如“机票买好了”,“电影看过没有”,就可以视为“机票(被)买好了”,“电影(被)看过没有”。也可以视为省略主词的“(我)机票买好了”,“(你)电影看过没有”。
中文里被动观念原来很淡,西化之后,凡事都要分出主客之势,也是自讨麻烦。其实英文的被动句式,只有受者,不见施者,一件事只呈现片面,话说得谨慎,却不清楚。“他被怀疑并没有真正进过军校”:究竟是谁在怀疑他呢?是军方,是你,还是别人?
前引五句的被动语气都很拗口,应予化解。句三十八可改成:“这一项提案执行委员会已经讨论多次,而且通过了。”句三十九可改成:“那名间谍奉命在火车站的月台上等候他。”以下三句也可以这么改写:句四十:“千千万万的读者正抢购这本新书。”句四十一:“基辛格在后人的记忆里,不外是一位翻云覆雨的政客。”(或者:“历史回顾基辛格,无非是一位翻云覆雨的政客”。)句四十二:“他出身低下,却一直瞒着所有的部属。”
(四十三)献身于革命的壮烈大业的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四十四)人口现正接近五百万的本市,存在著严重的生存空间日趋狭窄的问题。
(四十五)男女之间的一见钟情,是一种浪漫的最多只能维持三四年的迷恋。
英文好用形容词子句,但在文法上往往置于受形容的名词之后,成为追叙。中文格于文法,如要保留这种形容词子句的形式,常要把它放在受形容的名词之前,颤巍巍地,像顶大而无当的高帽子。要化解这种冗赘,就得看开些,别理会那形容词子句表面的身份,断然把它切开,为它另找归宿。
前引三句不妨分别化为:句四十三:“他献身于革命的壮烈大业,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句四十四:“本市人口现正接近五百万,空间日趋狭窄,问题严重。”句四十五:“男女之间的一见钟情,是一种浪漫的迷恋,最多只能维持三四年。”英文里引进形容词子句的代名词和副词如which、who、where、when等等,关节的作用均颇灵活,但在中文里,这承先启后的重担,一概加在这么一个小“的”字上,实在是难以胜任的。中文里“的,的”成灾,一位作家如果无力约束这小“的”字,他的中文绝无前途。
(四十六)当你把稿子写好了之后,立刻用挂号信寄给编辑。
(四十七)当许先生回到家里看见那枝手枪仍然放在他同事送给他的那糖盒子里的时候,他放了心。
(四十八)你怎么能说服他放弃这件事,当他自己的太太也不能说服他的时候?
英文最讲究因果、主客之分——什么事先发生,什么事后来到,什么事发生时另一件事正好进行到一半,这一切,都得在文法上交待清楚,所以副词子句特别多。如此说来,中文是不是就交代得含糊了呢?曰又不然。中文靠上下文自然的顺序,远多于文法上字面的衔接,所以貌若组织松懈。譬如治军,英文文法之严像程不识,中文文法则外弛内张,看来闲散,实则机警,像飞将军李广。“当……之后”、“当……的时候”一类的副词子句,早已滥于中文,其实往往作茧自缚,全无必要。
最好的办法,就是解除字面的束缚,句法自然会呼吸畅通。句四十六可简化为:“你稿子一写好,立刻用挂号信寄给编辑。”句四十七只须删去“当……的时候”之四字咒,就顺理成章,变成:“许先生回到家里,看见那枝手枪仍然放在他同事送给他的那糖盒子里,就放了心。”句四十八的副词子句其实只关乎说理的层次,而与时间的顺序无涉,更不该保留“当……的时候”的四字咒。不如动一下手术,改作:“这件事,连他自己的太太都无法劝他放手,你又怎么劝得动他?”
(四十九)我决不原谅任何事先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擅自引述我的话的人。
(五十)那家公司并不重视刘先生在工商界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经历的这个事实。
(五十一)他被委派了明天上午陪伴那位新来的医生去病房巡视一周的轻松的任务。
英文里的受词往往是一个繁复的名词子句,或是有繁复子句修饰的名词。总之,英文的动词后面可以接上一长串字眼组成的受词,即使节外生枝,也顿挫有致,不嫌其长。但在中文,语沓气泄,虎头蛇尾,而又尾大不掉,却是大忌。前引三句话所以累赘而气弱,是因为受词直到句末才出现,和动词隔得太远,彼此失却了呼应。
这三句话如果是英文,“任何人”一定紧跟在“饶恕”后面,正如“事实”和“任务”一定分别紧跟着“重视”和“委派”,所以动词的作用立见分晓,语气自然贯串无碍。中文往往用一件事做受词(字面上则为短句),英文则往往要求找一个确定的名词来承当动词:这分别,甚至许多名作家都不注意。例如“张老师最讨厌平时不用功考后求加分的学生”,句法虽不算太西化,但比起“张老师最讨厌学生平时不用功,考后求加分”来,就没有那么纯正、天然。
同样,“我想到一条可以一举两得的妙计”也不如“我想到一条妙计,可以一举两得”。关键在受词是否紧接动词。兹再举一例以明。“石油涨价,是本周一大新闻”比“石油的涨价是本周一大新闻”更像中文,因为前句以一件事(石油涨价)为主词,后句以一个名词(涨价)为主词。
要化解句四十九至五十一的冗赘,必须重组句法,疏通关节,分别改写如下:句四十九:“任何人事先没有得到我同意就擅自引述我的话,我决不原谅。”句五十:“刘先生在工商界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经历,这件事,那家公司并不重视。”句五十一:“院方派给他的轻松任务,是明天上午陪伴那位新来的医生去病房巡视一周。”(或者:他派定的任务轻松,就是明天上午陪伴那位新来的医生,去病房巡视一周。)
以上所论,都是中文西化之病。当代的白话文受外文的影响,当然并不仅是西化。例如在台湾文坛,日本文学作品的中译也不无影响,像林文月女士译的《源氏物语》,那里面的中文,论词藻,论句法,论风格,当然难免相当“和化”。读者一定会问我:“中文西化,难道影响全是反面效果,毫无正面价值吗?”
当然不尽如此。如果六十年来的新文学,在排除文言之余,只能向现代的口语,地方的戏曲歌谣,古典的白话小说之中,去吸收语言的养分——如果只能这样,而不曾同时向西方借镜,则今日的白话文面貌一定大不相同,说不定文体仍近于《老残游记》。
也许有人会说,今日许多闻名的小说还赶不上《老残游记》呢。这话我也同意,不过今日真正杰出的小说,在语言上因为具备了多元的背景,毕竟比《老残游记》来得丰富而有弹性。就像电影的黑白片杰作,虽然仍令我们吊古低回,但看惯彩片之后再回头去看黑白片,总还是觉得缺少了一点什么。
如果六十年来,广大的读者不读译文,少数的作家与学者不读西文,白话文的道路一定不同,新文学的作品也必大异。中文西化,虽然目前过多于功,未来恐怕也难将功折罪,但对白话文毕竟不是无功。犯罪的是“恶性西化”的“西而不化”,立功的是“善性西化”的“西而化之”以致“化西为中”。其间的差别,有时是绝对的,但往往是相对的。除了文笔极佳和文笔奇劣的少数例外,今日的作者大半出没于三分善性七分恶性的西化地带。
那么,“善性西化”的样品在哪里呢?最合理的答案是:在上乘的翻译里。翻译,是西化的合法进口,不像许多创作,在暗里非法西化,令人难防。一篇译文能称上乘,一定是译者功力高强,精通截长补短化淤解滞之道,所以能用无曲不达的中文去诱捕不肯就范的英文。
这样的译文在中西之间折冲樽俎,能不辱中文的使命,且带回俯首就擒的西文,虽不能就称为创作,却是“西而化之”的好文章。其实上乘的译文远胜过“西而不化”的无数创作。下面且将夏济安先生所译《古屋杂忆》(The Old Manse: by Nathaniel Hawthorne)摘出一段为例:
新英格兰凡是上了年纪的老宅,似乎总是鬼影幢幢,不清不白,事情虽怪,但家家如此,也不值得一提了。我们家的那个鬼,常常在客厅的某一个角落,喟然长叹;有时也翻弄纸张,簌簌作响,好像正在楼上长廊里研读一篇讲道文——奇怪的是月光穿东窗而入,夜明如画,而其人的身形总不得见。
夏济安的译文纯以神遇,有些地方善解原意,在中文里着墨较多,以显其隐,且便读者,不免略近意译,但译文仍是上乘的,不见“西而不化”的痕迹。
再从乔志高先生所译《长夜漫漫路迢迢》(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by Eugene O'Neill)录一段对话:
你的薪水也不少,凭你的本事要不是我你还赚不到呢。要不是看你父亲的面子没有一家戏园老板会请教你的,你的名声实在太臭了。就连现在,我还得不顾体面到处替你求情,说你从此改过自新了——虽然我自己知道是撒谎!
夏济安的译文里,成语较多,语气较文,句法较松动。乔志高的译文句法较紧,语气较白,末句更保留倒装句式。这是因为夏译要应付19世纪中叶的散文,而乔译面对的是20世纪中叶的对白。二译在文白上程度有异,恐怕和译者平日的文体也有关系。兹再节录汤新楣先生所译《原野长宵》(My Antonia: by Willa Cather):
隆冬在一个草原小镇上来得很猛,来自旷野的寒风把夏天里隔开一家家庭院的树叶一扫而光,一座座的房屋似乎凑近在一起。屋顶在绿荫中显得那么远,而现在却暴露在眼前,要比以前四周绿叶扶疏的时候难看得多。
三段译文相比,夏译不拘小节,几乎泯灭了原作的形迹;乔译坚守分寸,既不推衍原作,也不放任译文;汤译克己礼人,保留原作句法较多,但未过分委屈中文。换句话说,夏译对中文较为照顾,汤译对于原作较为尊重,乔译无所偏私。
三段译文都出于高手,但论“西而化之”的程度,夏译“化”得多,故“西”少;汤译“化”得少,故“西”多;乔译则行平中庸之道。纯以对中文的西化而言,夏译影响不大——输入的英文句法不多,当然“教唆”读者的或然率也小。汤译影响会大些——输入的英文句式多些,“诱罪率”也大些;当然,汤译仍然守住了中文的基本分寸,所以即使“诱罪”,也无伤大雅。

本文旨在讨论中文的西化,无意深究翻译,为了珍惜篇幅,也不引英文原作来印证。“善性西化”的样品,除了上乘的译文之外,当然还有一流的创作。
在白话文最好的诗、散文、小说,甚至批评文章里,都不难举出这种样品。但是并非所有的一流创作都可以用来印证,因为有些创作的语言纯然中国韵味,好处在于调和文白,却无意去融会中西。例如梁实秋先生精于英国文学,还译过莎氏全集,却无意在小品文里搞西化运动。
他的《雅舍小品》享誉已久,里面也尽多西学之趣,但在文字上并不刻意引进英文语法。梁先生那一辈,文言底子结实,即使要西化,也不容易西化。他虽然佩服胡适,但对于文言的警策,不肯全然排斥,所以他的小品文里文白相济,最有弹性。比他年轻一辈而也中英俱佳的作家,便兼向西化发展。且看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流苏吃惊地朝他望望,蓦地里悟到他这人多么恶毒。他有意的当着人做出亲狎的神气,使她没法可证明他们没有发生关系。她势成骑虎,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爷娘,除了做他的情妇之外没有第二条路。然而她如果迁就了他,不但前功尽弃,以后更是万劫不复了。她偏不!就算她枉担了虚名,他不过口头上占了她一个便宜。归根究底,他还是没得到她。既然他没有得到她,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
张爱玲的文体素称雅洁,但分析她的语言,却是多元的调和。前引一段之中,像“势成骑虎”、“前功尽弃”、“万劫不复”等都是文言的成语:“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爷娘”近乎俚曲俗谣:“蓦地里悟到”,“枉担了虚名”,像来自旧小说,至少巴金的小说里绝少出现;其他部分则大半是新文学的用语,“他还是没得到她”之类的句子当然是五四以后的产品。最末一句却是颇为显眼的西化句,结尾的“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简直是英文的介系词片语,或是分词片语——译成英文,不是with better terms of peace,便是bringing better terms of peace.这个修饰性的结尾接得很自然,正是“善性西化”的好例。下面再引钱钟书40年代的作品《谈教训》:
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著高尚到一般人所不及的理想,更有跟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骄傲和力量。
这显然是“善性西化”的典型句法,一位作家没有读通西文,或是中文力有不逮,绝对写不出这么一气贯串、曲折而不芜杂的长句。这一句也许单独看来好处不很显眼,但是和后面一句相比,就见出好在哪里了:
当上帝要惩罚人类的时候,他有时会给予我们一个荒年,有时会给予我们一次瘟疫或一场战争,有时甚至于还会创造出一个具有着高尚到一般人所不及的理想的道德家——这道德家同时还具有着和这个理想成正比例的骄傲与力量。
后面这一句是我依“恶性西化”的公式从前一句演变来的。两句一比,前一句的简洁似乎成了格言了。
我想,未来白话文的发展,一方面是少数人的“善性西化”愈演愈精进,一方面却是多数人的“恶性西化”愈演愈堕落,势不可遏。颇有不少人认为,语言是活的,大势所趋,可以积非成是,习惯成自然,一士谔谔,怎么抵得过万口嗫嗫,不如算了吧。一个人抱持这种观念,自然比较省力。但是我并不甘心。
一个民族的语言自然要变,但是不可以变得太快,太多,太不自然,尤其不可以变得失尽了原有的特性与美质。我们的教育界、文化界和各种传播的机构,必须及时警惕,须为良谋。否则有一天“恶性西化”的狂潮真的吞没了白话文,则不但好作品再无知音,连整个民族的文化生命都面临威胁了。
余光中先生写于197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