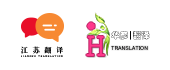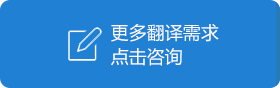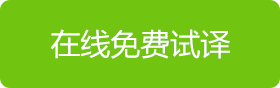就“一带一路”倡议而言,其内容可以归结为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两部分。硬件建设是指跨国间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经济贸易的合作与发展,软件建设是指对跨国间语言、文化、宗教、教育制度、法律等的相互了解、理解、遵守与应用。硬件发展是物质建设,软件发展属精神建设。需要注意的是硬件建设进行时需要语言的沟通。

就全球范围的多元文明而言,不同语言的接触和沟通,或“对话”,可区分5种方式,即不同民族间的对话、贸易和商业层面的对话、外交和国家层面的对话、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的对话,以至当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矛盾不可调和时导致的“丛林法则”——通过战争进行强迫性的对话。上述5种对话方式可进一步分为建设性及非建设性或破坏性两大类。民族、贸易和外交的对话基本上是建设性的对话;宗教对话有建设性的一面,也有非建设性的一面;战争则基本上属于破坏性对话。今天,为了推动世界多元文明的交融和发展,我们关心的是建设性对话,以便最大限度地维护文明之间的平等交往,抑制文明间的冲突。积极进行建设性对话,就是不同文明之间最大的文化尊重。
没有语言,不同民族之间的对话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例如,2015年5月14日印度总理莫迪参观我国西安大兴善寺留言,书写时用的是他家乡的古吉拉特语(Gujarati,印度宪法规定的官方语言之一),我国在场者无人能看懂。后经一位印度留华学生托人把该留言译成印地语,然后把印地语译成英语,最后由英语译为汉语。不难发现,莫迪当时完全可用英语或印地语留言,但他考虑的不是现场的沟通,而是具有深远的意图,他利用参观大兴善寺的机会宣传和捍卫他家乡的古吉拉特语。事实也表明,我国对印度语言的研究和教育,过去的确限于英语和印地语,懂得印度本地强势语言的外语人才非常罕见。
正因为如此,不论是推动“一带一路”,还是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国家的语言战略规划,在维护国际话语权上一方面要维护汉语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一方面要尊重其他民族和国家的语言。
就现有材料看,美国一直在积极倡导英语作为“世界语言”进入各国教育体系,影响各国语言、文化发展,形成“语言霸权”。9·11事件后,美国陆续出台《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国防语言转型路线图》《语言与区域知识发展计划》《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和文化能力战略规划(2011—2016)》等多项语言政策规划和举措。俄罗斯国防部负责确定国防领域关键外语语种,在高校储备的外语资源多达145种,涉及覆盖世界多国和地区的9大语系及其下属语种。法语在全球推广,为法国文化发挥超出其国力的影响立下汗马功劳。英国出台的“国家语言战略”则为维持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提供助力。
就我们国家来说,对语言战略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已提上日程。

2018年9月在湖南长沙召开了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这是联合国“2019年国际本土语言年”的一个重要活动, 参加人员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关领域的官员、专家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穆兹·查楚克在大会开幕式致辞中说,语言的使用,决定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保护语言资源,促进语言多样性,近年来通过搭建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在线平台、开展国际本土语言年活动等举措,帮助世界各国提升语言资源保护意识、关注语言消亡加剧等现实问题。大会最后通过并发表了《岳麓宣言(草案)》,呼吁更多国家和地区关注此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要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显然,这“五通”,都需要语言铺路。语言互通是实施“五通”的基础。陆俭明(2016)进一步指出,要让语言为“一带一路”建设铺路搭桥,便要求增强语言意识,要有一定的规划和管理机构,要立即着手制定“一带一路”总体的语言规划和顶层设计,要加快培养语言人才,包括培养通晓沿线沿路国家语言的语言人才和为沿线沿路国家培养精通汉语的人才。
如果说陆俭明是从学术角度发表专家意见,那么我国在2019年召开的两会中,很多参会代表提出建议,其内容为“针对‘一带一路’国家的需求培养一批专门化人才, 同时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了解‘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 掌握多门外语的综合型、外向型人才, 促进软实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