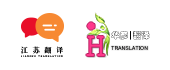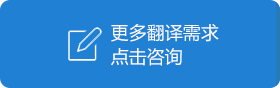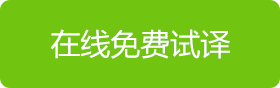有不少朋友想做翻译,又不了解情况,经常会问我关于翻译的问题:翻译好不好做,会不会有什么困难,等等。我虽然最近几年没有翻译过书了,但基于之前积攒的经验,还是可以给出明确建议:翻译难做。
这条建议时常会遇到质疑。许多朋友会说:我虽然没有做过翻译,但我看英文没啥问题。翻译,不就是看懂英文转换成中文嘛。为什么你说那么难?
这么说的人,往往没有译者体验,只有读者体验,所以翻译无非是让读者从“读原文”变成“读译文”。如果真的当过译者,翻译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起码,下面几大困难是任何译者都躲不掉的。
一支笔画不出百样色彩
即便译者倾尽全力,彻底理解了原文,仍然会让读者不满意,因为译文剥夺了读者的“解释权”。
什么是读者的解释权?简单说,就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汉姆雷特”。原文里怎么写的,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和想象,大家都有按照自己的体验、经验、想象去理解原文的权利。
译者却不同,译者首先是读者,他对原文当然有自己的理解,这是作读者的权利。另一方面,译文的那“一千个读者”仍然期望看到一千个汉姆雷特。然而这时候,译者的理解已经熔铸在翻译里,印刻在译文中,针对原文的众多解释和想象就此消失了。挑剔的读者,尤其是能读原文的读者,往往会感到不满意。
仍然举上面那段“传输数据”的文本的例子。在我看来,可能产生误解的根源在于原作者举例时不够仔细。如果我是作者,我不会说“完整交互总共需要传输100K的数据,目前已经传输了50K,所以要关心的只有50K数据”,而是改为“完整交互总共需要传输100K的数据,目前已经传输了60K,所以要关心的只有40K数据”,避免出现误解。
但只有身为作者,这种改动才可以理直气壮,译者没有百分百的理由和权利去修改原文。对这样的修改,许多读者并不买账,因为它“不忠于原文”。
我在讲翻译时曾写过,英文里的许多a其实只是语法需要,一律翻译成“一个”反而显得累赘。比如“每个地方都有一位负责的人,一个县应当有一位县长,一个市应当有一位市长,一个省应当有一位省长”就很累赘,地道的说法是“每个地方都有个负责人,县有县长,市有市长,省有省长”。
觉得没问题,对吧?我们看看更复杂的例子:“他好像一个独翼的天使,矗立在一张门前,死死盯住远方的一棵树”。按照上面的逻辑,更好的翻译似乎是这样的:“他好似独翼的天使,矗立门前,死死盯住远方的树”。
这个例子得到不少人的赞同,但也有不只一人反对,理由是“原文里连续出现的a,原作者应当是有特别用意,要表达孤单的感觉,一律去掉,反而改变了原文的韵味”。这种说法有道理吗?不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严格照原文翻译也有不少读者反对,理由是过多的“一个”完全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
这个问题的根源不在译者,而在翻译。毕竟,原文的解释和想象的权利完全属于原文读者,一旦进入翻译,就必然剥夺一些针对原文的解释和想象。同样一段文字,你看来平淡无奇,我觉得微言大义,他认为别有所指。这种分别很微妙,较真就容易吵起来。但是,又没有绝对的、客观的对错标准,因为个人的理解本来就可以不同。所以文艺理论才会说,作品一旦写成,它就与作者脱钩,完全存在于读者的理解和阐释之中。
鲁迅先生写过:我家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为什么要这么写?为什么不直接说“两颗都是枣树”?这些问题历来争论不休,不同人有不同理解。我估计就是鲁迅先生再世,未必也能给出大家信服的答案。译者如果遇到这种句子,无论怎么翻译,都得不到全部读者的认同。
一支笔画不出百样色彩,这始终无解的难题,是译者的宿命。
一张口难吃百家饭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汉姆雷特”,说的是读者的理解各异。其实除去读者的理解,原文涉及的领域也可能包罗万象。同样的概念,在一千个领域可能有一千种名称。不了解领域的行话,给不出“接地气”的说法,就会给读者感觉“出戏”、“外行”,这也是译者面临的难题。
比如specification,IT领域通常翻译为“参数指标”,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涉及到某些工业领域,就必须摇身一变,行话叫“规格说明”。具体到军工系统、武器制造,又得改头换面,叫做“性能诸元”。如果译者不了解这些,造出“火炮性能参数”,或者“软件系统规格”,读者就容易有意见。
再比如range,一般翻译为“范围”。但在IT领域,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就要翻译为“近距离通讯”,进入武器系统,short range missle就要翻译为“短程导弹”,交战中的in range更是应当翻译为“进入射程(已在射程内)”。
实际上,在翻译中类似的讲究很多,而且这类讲究没有固定规章可循,全凭译者平时留意。
比如-ist,一般说的“xx主义者”没错,但涉及到政局便有不同。“议会中的国际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各占半数”就明显别扭,符合习惯的翻译是“议会中的国际派和本土派各占半数”。还有international community,翻译为“国际社群”会笑掉大牙,约定俗成的翻译是“国际社会”,虽然community似乎和society一点关系也没有。
哪个人告诉你-ist翻译为“派”,哪本书告诉你community翻译为“社会”?没有,全靠译者平时用心,吃百家饭。如果没吃过百家饭,译文不自然、不地道就是必然的结果。我之前翻译《精通正则表达式》就吃过亏。
《精通正则表达式》的作者是美国人,大概美国人都对车很了解,所以原作者在讲解“水面下”的正则表达式匹配原理时,大量使用了汽车的例子:打开引擎盖,这里是分电盘,那里是变速箱……。
可惜,等我能把发动机舱里的东西都分得清楚,是交稿两年之后的事情了。在翻译的时候完全不熟悉车主们的行话,所以transmission到底翻译为“变速箱”还是“传动机构”,似乎总说“变速箱”也有点别扭…… 所以今天再看这段译文,虽然花了不少心思,还是不够地道。
不但国内有百家饭,国际上也有百家饭。我就见过译文里出现的“日本外交部长”。没错,foreign minister通常的翻译正是“外交部长”,“日本外交部长”干的确实是“外交部长”的活。但译者需要知道,在日本这个职位有专门的称呼,叫“外相”或“外务大臣”。由此类推,日本内阁的Chief Secretary也不是“秘书长”,而是“内阁官房长官”。
百家饭不只关系当下,还涉及历史。同样的概念,不同时代的称呼也不同。麻烦的是,一般词典并不会涉及“历史称呼”,所以更要靠译者平时留心。比如foreign affairs,如今大家都知道叫“外交事务”,往前倒推一百多年,晚清的说法是“洋务”,再往前几十年,就得叫“夷务”。不懂得这些,译文就会显得跳脱、错位。
译者怎么能懂得各种领域的行话?没有太多好办法,只能平时自己多留意,把各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起来。